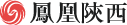舊址:探訪寶雞第一戰俘看守所
2015年08月11日 09:15
來源:陜西傳媒網—三秦都市報
太寅村三組村民張來貴向記者講述大同學園當年的情形 寶雞第一戰俘所關押的日軍戰俘 寶雞第一戰俘所俘虜在接受審訊 原標題:探訪寶雞第一戰俘看守所 500名戰俘中300多人為八路軍俘獲 在寶雞市渭濱區
500名戰俘中300多人為八路軍俘獲
據官方統計,第一戰俘收容所設立期間,先后接收了來自華中、華北等戰場押送來的戰俘男女約500人,其中300多名日軍戰俘是被我黨領導的八路軍俘虜的。在1939年以前,八路軍還沒有形成戰俘管理制度,日軍戰俘上交國民政府看押監管。1939年后,延安成立了自己的戰俘管理所,戰俘也就不再轉往寶雞管理所。此外,由于路途遙遠,轉送后方不能保證安全,很多根據地也成立了自己的俘虜看守機構,很多俘虜被轉化,成為反戰同盟的一員,又返回了前線作戰,很多俘虜甚至為此犧牲在抗日前線。
如今豎立在寶雞“第一俘虜收容所”遺址門口的《大同學園碑記》記載:收容所開設的科目有三民主義、國際形勢、中日關系史、中文、音樂等,通過上這些課讓戰俘明白國際形勢,了解中日兩國歷史上的友好交往,認識到戰爭的罪惡,自覺地抵制戰爭。
日本俘虜山本是清和天皇第25代孫,被俘前系日偽國民政府河南省建設廳的顧問,由于受過高等教育,在戰俘中頗有號召力。1940年夏,他組織戰俘趁大雨集體夜逃。被抓回隔離禁閉期間突患重病,自以為不被處以極刑也得病死。但戰俘所的看守人員很快把他送到寶雞縣醫院治療。入院次日,汪大捷親自前往探視。后來山本在寫給汪所長的信中主動披露了自己的身份:“作為清和天皇第25代孫,祖先是開拓北海道的功臣……帝國思想是不能改變的,但是大同學園的人道主義、大同思想和自己身受對戰俘的優待,我信服了……”
第一俘虜收容所(大同學園)擁有監管的官兵三十多名,負責看押戰俘的軍隊在外面,有一個營和一個憲兵排的兵力。在押的日軍戰俘中陸軍居多,也有少數空軍,文化程度高低不一。
1940年秋,戰俘押切五郎與田中照子因違反“所規”畏罪潛逃。到第三天又主動回來了,心知難免重罰,甚至會被處死。不料戰俘所念他們主動回來認罪,只令其寫悔過書,免去了處罰。
據資料顯示:多數服從關押、遵守所規的男俘集中管押在所內,少數串通鬧事、企圖逃跑的20個男俘分別關押在所外的溝道里、北崖上、桑園里、崖底下等幾處民房和窯洞內,設崗哨臺看管。其中桃學三郎(音)因煽動在押人員暴動也被槍決。另外,關押在一位韓姓村民家中的戰俘冢塬力一(音)也因為參與組織暴動而被槍決在村外的一個土坯房內。
據渭濱區博物館館長郝明科研究考證,在第一戰俘所死亡的戰俘中,有一部分是得病而死,有一部分拒絕治療,還有一小部分頑劣分子出逃或者繼續做惡,得到了應有的制裁。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1946年4月下旬,“大同學園”內近500名戰俘在部隊的押送下,坐火車遣返回國。
退休老教師心目中的“戰俘印象”
“戰俘有將近一百人,都穿著灰色衣服,頭剃的‘倍兒’亮,像大頭和尚,而當兵的只來了三十多人,有的村民對日本人怒目而視……”時隔70多年,太寅村村民、退休老教師張尚仁老人仍然記得他第一次見到日軍戰俘時的情形。
1939年夏,張尚仁當時剛剛年滿16歲,他正坐在村口麥場的大槐樹下乘涼,突然,他看到由村西的河道里上來一支著裝各異的部隊,其中一些人相互攙扶、還拄著拐杖。驚慌的村里人以為“日本鬼子來了”急忙趕著牲口,把剛收的糧食往山里藏。
今年92歲的張尚仁是太寅村里唯一見證了那段“日軍戰俘改造”的老人,遺憾的是記者采訪時,老人剛剛仙逝不久,但在老人生前撰寫的回憶錄和談話記錄中記者看到:“在收容所里一名叫金志杰的翻譯后來就一直住在我們家。當年(中國老百姓)日子很苦,但戰俘們享受的仍然是中國軍隊上等兵的待遇。夏天一套單衣,冬天一套棉衣,還有被褥毛毯。雖然吃大米白面的機會不是很多,但吃飽不成問題,他們大部分時間和村民一樣,吃的是苞谷面。戰俘使用河灘里的水磨磨面,他們愛穿木板鞋,對黃豆和山野菜有偏愛。”
參加學習的戰俘,會在管理人員的組織下制作一些如躺椅、筷子、手杖、玩具、肥皂盒之類的物品,有些學員編織的毛衣毛褲、圍巾手套等很受村民的喜愛。制作工藝品的時候,戰俘都是跪坐在墊子上,一些學員堅持不愿做槍炮玩具,以示對戰爭的深惡痛絕。由于產品受到歡迎,戰俘所在寶雞縣城西街租用了一間房子,專門銷售學員制作的物品,所賣之錢全數兌現給物品制作者。戰俘們把掙到的錢用于購買香煙,或者在村里的小店買一些醬菜改善生活。
第一戰俘所正在申請“愛國主義教育基地”
1941年春,寶雞第一戰俘收容所首任所長汪大捷因帶領俘虜郊游寫生,被控告“縱兵擾民”等候處理。雖然最終被判無罪恢復了名譽,但他還是在復雜的派系斗爭中淚別大同學園。接任汪大捷的先后是國民軍少將王丕云和馬益祥。
汪大捷曾兩度留學日本,畢業于東京帝國大學。他第二次留學期間恰逢中國受到日本侵略,因鼓動留學生鬧事而被驅逐回國。1946年,汪大捷任熊式輝的少將級秘書。全國解放時,他毅然留在大陸,并參加了中國人民志愿軍,轉業后在北京對外經濟貿易大學任教授。1972年中日建交后,汪大捷赴日講學,并受聘主編《日英漢科學技術大辭典》。他客居日本,積極從事中日友好活動。
1994年8月21日,時隔53年后,第一戰俘所大同思想倡導者汪大捷終于在兒媳和陜西省文史研究館館員張光祖的陪同下再次踏上太寅村。寶雞市文物局在各方的努力下,于2000年8月15日于收容所原址上立碑。同年,汪大捷先生去世,其后人將其骨灰葬于碑后。
汪所長去世了,但是關于“大同學園”和第一戰俘所的故事并沒有終結,從1998年起,渭濱區博物館館長郝明科在寶雞市文物局原局長張潤堂的幫助下,走訪當地群眾,收集歷史證據,進行實地考察,形成了累計10萬字的《“第一戰俘營”調查研究報告》和《鑒史明志為和平追憶“大同”壯國威》的演講稿,應邀多次到學校、部隊、機關企業進行愛國主義教育演講。
據悉,2014年,寶雞市渭濱區檔案局和渭濱區文物旅游局正式申請將第一戰俘收容所遺址命名為“愛國主義教育基地”,目前正在等候上級的批復和認定。相信不久的將來,那段難忘的歷史將再次呈現在人們面前…… 文/圖本報記者 楊立 實習生 李文博
頻道推薦
智能推薦
圖片新聞
視頻
-

滕醉漢醫院耍酒瘋 對醫生大打出手
播放數:1133929
-

西漢海昏侯墓出土大量竹簡木牘 填史料空缺
播放數:4135875
-

電話詐騙44萬 運營商被判賠償
播放數:2845975
-

被擊落戰機殘骸畫面首度公布
播放數:535774